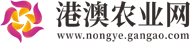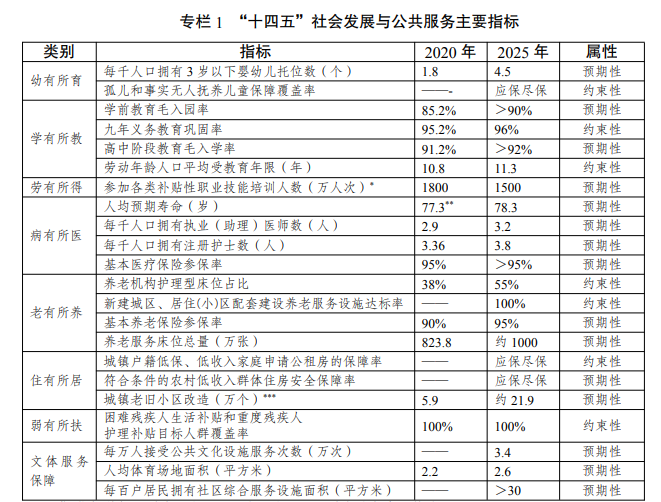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纵观马伯庸的小说序列,新作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多少有些“另类”。先说“部头”,十万字的篇幅,相比马伯庸过去任何一部作品,都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简短和精悍;再说“题材”,虽然影射职场是马伯庸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,但跳出历史叙事,转而借壳神话,于他来说还是“首秀”。
但倘若深究起来,马伯庸与西游故事的“联手”,早已有迹可循。5年前,马伯庸在某网络平台开设一档有声节目,解读22本冷门书籍,作为《西游记》三大续书之二的《后西游记》《西游补》双双入选,足见他对西游故事情有独钟也深有研究。或许正是受到《后西游记》《西游补》等同人小说“人设反转”的启示,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里的太白金星、孙悟空、观音、唐僧等,也都一改其根深蒂固的性格特征,转而被赋予新的精神内核,比如总是情绪饱满、充满活力的孙悟空,到了马伯庸笔下却变得心事重重、忧郁颓废;又比如,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中的唐僧,既不完全像原著《西游记》里那般优柔寡断、临危即乱,也没法和《后西游记》里“逆袭”出的镇定自若、处变不惊画上等号,而是跳离了两者单一扁平的“神性”设置,让这个更具现代职场感的人物形象,有时表现得骄横傲慢、目中无人,有时又舍身担当、自我牺牲,在看似矛盾混杂之中,彰显出真实饱满、有血有肉的独特“人性”。
如果说,阅读《西游记》及其续书,有如以俗世之眼旁观仙境魔界之奇崛;那么,看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,就好比是把那些存活在另一个生命体系中的神魔鬼怪,统统拉入到人世之中,让他们和我们这些食五谷、生百病的普通人一样,拥有了烦恼和快乐,也拥有了欲望和纷争。虽然小说以“太白金星”作为书名的一部分,但在情节叙述中,马伯庸却很少使用“唐僧”“太白金星”“财神”这些具有神明性质的称谓,而是以玄奘、李长庚、赵公明等原名代指,特别是“太白金星”李长庚,还时常是其他神仙口中的“老李”或者“小李”,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息,早已是一个如假包换的“身边人”。
现如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通信、交通方式,也都在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中变着法子地呈现。小说中传递信息的“飞符”就好似我们当下形影不离的“微信”,往来天宫之间的“推云童子”就如同走街串巷的“快车司机”,可以随时拨号通话的“笏板”则不难让人联想到“手机”。此外,化妆、打赏、报销、碰瓷、订购服务等一系列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,也都毫不违和地融入在小说情节之中,既平添了时空穿越的奇幻,也兼具感同身受的妙趣。
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因循的当然是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框架,但小说借用了吴承恩的“形”,被赋予的却是马伯庸的“魂”。在《西游记》第二十四回里,镇元子与孙悟空身份悬殊的结拜,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津津乐道的“叙述空白”,学者刘再复就认为此情节是吴承恩对“道释两家虽有纷争但可以情同手足”的隐喻,但马伯庸则试图“化复杂为简单”,小说补白道,镇元子因先后与观音、玄奘结拜不成,退而求其次找上孙悟空,而后者又是一副“懒得躲闪,随便他怎么摆弄”的态度,这才结拜成功。在第三十一回里,百花羞之子被“掼做肉饼”的情节,可谓是《西游记》的“血腥之最”,马伯庸既没有顺应原著,也没有改写原著,而是“化残忍为不忍”,明面上让两子之死记录在了观音的揭帖里交差,暗地里却安排李长庚救下孩子,让他们洗去记忆当起供奉童子。
清人张书坤对《西游记》的阐释是“人生斯世,各有正业,是即各有所取之经,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”。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沿用《西游记》的情节,却辗转于详略之间,讲述着似是而非的故事,马伯庸大概是想说“人生斯世,皆有烦恼,与其亦步亦趋,不如从心所欲”。(易扬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