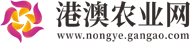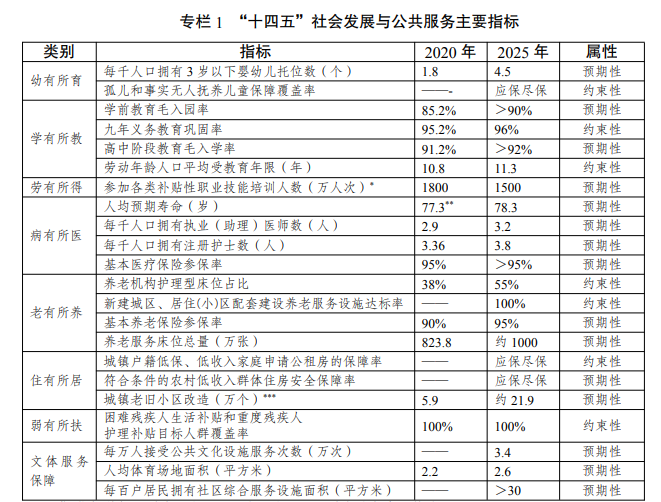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贾樟柯导演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(2018)剧照
蔡姑妈是我爸爸的老同事。我爸爸到曙光钟表店工作的那年,她才十八岁,他还叫过她“春秀妹妹”。我们家影集里有一张春秀年轻时的照片:瓜子脸,笑生双靥,颇有几分水秀,梳两根长辫子。我出生的时候,是妈妈一个人去的医院,我爸爸让她“先去”,说他“就来”,我妈觉得痛得不行了又转回来一次叫他,他还不动,不慌不忙在上班。蔡姑妈第一个赶到医院,看到我,回店里告诉我爸爸:“是个儿子!”他很高兴,跑去医院,结果是我。
在我小时候,经常在钟表店修理车间玩的年头,蔡姑妈家里已经有两个大姐姐了。她家就在钟表店旁边,只隔一条小马路,位于三岔路口,是一栋两层旧房,可以上到楼顶去晾晒、观望。横的中山路,直的解放路,站在楼顶上转弯抹角可以看到270°,每天街头巷尾的人来人往、鸡飞狗跳,蔡姑妈尽收眼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条街上曾出过轰动全城的社会新闻,就是在她家门口发生的,她看得比谁都清楚。蔡姑妈无事不知。
修理车间里一人一桌拼成长排,每两排面对面并着,隔了过道则背对背。但进门的这一小块是个飞地,就只一人一桌,全都同向,一共四排。蔡姑妈是面对门外楼梯的第一排,所以谁来了也是她第一个知道。她后面是个很老很瘦的老头,我觉得他长得很像蔡姑妈家里的男人,究竟是不是呢?没法问。老头后面是万厚大,非常肥壮的中年汉子,跟他的名字绝配。万厚大后面就是我爸爸,我爸爸后面是材料柜,靠墙了。
一天蔡姑妈拿出两条新的红花手绢,说给我一条,她一条。她把手绢折成一只老鼠,顺便教我——左右翻折,一卷到底,中间是身子,一头伸出个角,另一头拉出来,是尾巴——往我口袋里一塞。
我把头凑近蔡姑妈的耳朵,低低地问:“那个,坐你后面的人,是不是,你屋里那个呀?”
我的声音太低了,因为不好说,也说得很断续,说了几遍蔡姑妈才听懂了。
“哦,不是。他好老喔!”她哈哈地笑起来。
蔡姑妈跟万厚大打过一架。万厚大人不算坏,但说话喜欢阴阳怪气的,又损,听起来很坏。
那天万厚大上班时放了个屁。春秀在前排就呸了一声。
“……喝了老子的屁,还吐壳壳。”万厚大说。
春秀一听就转身绕过桌子朝他扑过去。不晓得厚大动手没有,是大夏天,他穿个背心,春秀把他胸前抓出好几道。事后店里开会批评,万厚大跟女同志打架,要赔礼道歉,扣半个月工资。他后来再不敢惹春秀。
“我指甲缝里都是他的肉屑屑,他好肥哟!”几十年后蔡姑妈跟我讲起这事,哈哈大笑。
几十年后——那是九十年代中了,我爸爸生重病不再上班,几年下来,来看他的人少了。蔡姑妈也退休了,还是隔一阵就来一回,来就给他带几包维维豆奶。我爸爸自从做放疗化疗后就没再吃一口饭,每天只喝维维豆奶。他一生爱吃甜东西,放疗化疗摧毁了他的胃口,只有豆奶还能喝。每天他用大搪瓷缸冲几袋豆奶,够一天的量,凉了就放炉子上炖热,继续喝。维维豆奶真该请他去拍广告:“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,七年里,每天只喝我们的豆奶……”
七年后我爸爸走了。蔡姑妈闻讯来我家,坐下就大哭。哭后就问各种事情怎么办,医药费怎么结,要找哪些人。我们没找哪些人,就去医院结算了费用,按流程办了丧礼,钟表店的老职工们都来了,好几十人依次走下单位的大巴,都是我小时候天天见面的熟面孔:蔡姑妈、李妈妈、万厚大……只是从前年轻的他们都老了。我跟他们一一握手,站在台上致辞,感觉时间把人颠了个个儿——从前他们说,我听;现在我说,他们听。
之后准备安葬,蔡姑妈往我家跑了几趟,说公墓太贵,她去找附近山上的地,给山民一些钱就行了,她自己的爹就葬在那座山上。拗不过她热心撺掇,我们跟她去看了一次,要进山了,她远远指着山头说:“喏,我爸爸在那儿守门。”我们还是决定就在公墓。后来上坟,蔡姑妈也一起去了,之后再来我家一起吃顿饭。
蔡姑妈每天走东家串西家,东家长西家短,哪家的事她都知道都要管,退休在家,忙的事顶一个居委会主任的专职工作。一旦有事,她不仅出主意,还陪着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到处跑。我以我们家的事来测算,真不知道她的时间怎么够分配到那么多人事上。
她也经常约人出去玩,她的信息多,知道哪儿好玩。她来约我妈,我妈不去。我妈一个人在家看电视,除了买菜散步看病,哪儿也不去。有一回,去了,跟着一大帮婆婆妈妈们,去河对岸的村子里春秀的一个亲戚家。亲戚承包了一片桔园,秋天满树的蜜桔都熟了。春秀说:“你们都去摘桔子呀!”婆婆妈妈们就都去摘,摘了装在自己的包里,又吃又装,有说有笑。我妈说不好意思摘,就在那里吃了一个桔子。我也担心那天怎么收场,结果亲戚还留她们吃了饭才走。
不记得是哪一年的暑假,我大概有三十岁了,回宜昌跟妈妈在街上走,碰到蔡姑妈。蔡姑妈问我妈最近身体怎样,我妈照例答说,不好。蔡姑妈突然把我妈数落了一顿。“你总这样!”她说,“老说这里不好,那里不好。你这大姑娘乖,你就天天说你这病那病;你那个小的不听话不懂事,你就什么都不说,就由她什么都不管,你还倒过来管她。造孽你这个老大是个操心的,天天听你说这些她心里不得安生!……”妈妈听她数落不吭声,我在旁边听得呆了。——你怎么知道,蔡姑妈?你怎么说得这么准?我没有告诉过你啊,我当时也还没觉得不公平啊。
又过了十多年。我在美国,妈妈病危,我们辗转两天飞了又飞赶回来,再一天后她去世了。我回家去取东西,不知道该先办哪一样,找什么东西都找不着,四壁萧然,六神无主。这时有人敲门,我开门一看,蔡姑妈和李妈妈手挽手站在门口,我一下就哭起来。但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知道的,我妈妈是从医院回家洗澡再回医院后就昏迷了,没有跟谁联系,我回来也没有跟她们联系。
“你妈就是知道她要走了,才回家洗澡的呀!”蔡姑妈后来说,在我告诉她事情经过时。
妈妈的房子里堆满了各种东西,全是破烂不堪的东西,如果外人来看,肯定是会直接让收破烂的来全部拉走的,但那就是我父母几十年的全部家当。只有我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,它们是我对家、对父母的记忆,清走了我的家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我的确什么东西都找不到,包括我一直知道在哪儿的我父亲的公墓证,因为是买的双墓,给我妈妈下葬是需要的,但它就是不在一直在的五屉柜里。直到我办完丧事,再回家收拾,突然看见五屉柜上有一张折好的纸,打开看,就是公墓证,是妈妈放在那里的。
“哎!你妈就是知道她要走,所以把这个找出来放在桌面上呀!”蔡姑妈拍着手说。
是了,的确是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妈妈把我救了,没让我坠入一个可怕的深渊。她几十年备受各种病痛折磨,病一直紧紧抓住她不放,到最后她直觉终于要结束了。她已住院了一段时间,貌似好转,准备出院了,特地回家一趟洗个澡。在医院里是不方便洗澡,不过要出院了其实也不必提前回家一趟洗澡。她洗澡的同时还把衣服丢进洗衣机洗了,但没有晾,几天后我从美国回来才晾上了。妈妈把五屉柜里的公墓证找出来放在柜面上,再回医院,随即陷入昏迷。假如她早一步,在家就昏迷了,我的后半生将无法做人——没有人能联系到她,我不能,医生也不能,她将倒在家里多日不为人所知。巧的是,我偏偏知道医生的电话,因为之前妈妈告诉了我一声:“这回又是潘医生管我呢!”大约一年前我们网购了吸氧机送到家里,妈妈不会安装,是潘医生来我家给她安装的,所以我知道潘医生的电话。我在美国联系不上妈妈,打给潘医生,他说她好些了,快出院了。再过两三天我打我妈妈的电话,就是护士接的了:“她情况很不好!她从家里回到医院就昏迷了!”……
蔡姑妈无事不知,把我不知道的补齐,让我在心里不断反刍。
妈妈的丧礼上,我讲了蔡姑妈刚刚告诉我的一件事——
“你妈这一辈子,遭孽!”蔡姑妈说,“你爸爸脾气又怪,又不晓得体贴人,她又太吃得起苦。他们结了婚三年你妈才从广东迁过来,她坐火车到武汉,你爸爸到武汉去接她来宜昌。他们先来店里,我在楼上看到,嗨哟!你爸爸甩着两只手在前面走,你妈一个人挑着行李担子跟在后面!”
妈妈从几千里外挑过来的行李,我知道的就有:一副床板,一顶粗纱蚊帐,床单被面,四季衣服,客家人做擂茶的陶钵……
接下来的两年我家还有很不小的麻烦事。父母都不在了,天大的麻烦事也该我接下来扛到肩头。我回宜昌,还是蔡姑妈她们陪着我东奔西跑,并拿主意。蔡姑妈那年七十六了。“反正,我还能动么,我就要出门。容儿,你这么多白头发,你比我还老啦……”
再到2022年的年末,全国上下几乎所有人都病了一场。我打电话给八十岁的蔡姑妈,电话里听见人声嘈杂。“蔡姑妈,您怎么样了呀?”
“小容呀?我还好,发了一天烧,第二天就退了。谢谢你关心。但是我妹妹走了。我们现在一大家子人才从山上下来。”
2021.9.14;2022.11.19;2023.1.13
作者:蔡小容
编辑:钱雨彤
责任编辑:舒 明
*文汇独家稿件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