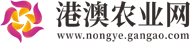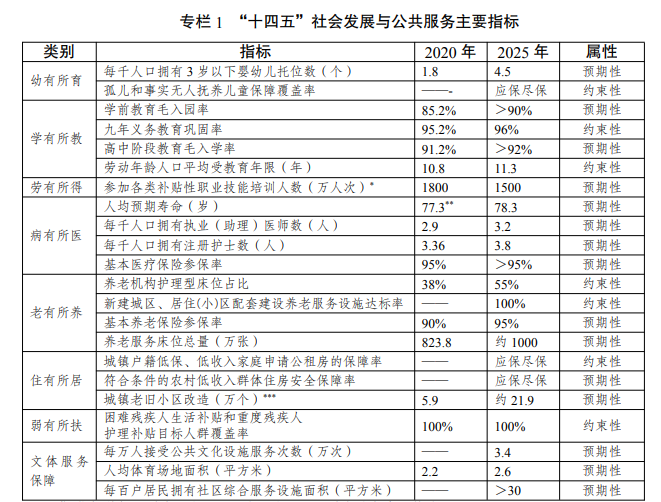文|灰狼
《漫长的季节》的精彩是全方位的,有精准达意的镜头调度,有真实还原的场景道具,当然也离不开全员A等的演技。这些要素,在本质上相辅相成,都离不开文本自身的厚度。或者说,剧本好,台词好,确实能在极大程度上激发导演的调度潜能、美术的塑形潜能以及演员们的表演潜能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《漫长的季节》(2023)
几个主演当中,人们会盛赞秦昊,因为他演出了另一幅皮囊和个性之下的同样的灵魂,最后的升华和泪点也都在他身上;人们也会为扮演马德胜的陈明昊感到震惊,他同张颂文一样,都是基础扎实情绪炸裂的方法派,是一直以来在影视剧中被深埋的宝藏演员。
配角中,大家主要表扬了林晓杰、蒋奇明、王佳佳,乃至任素汐和张静初,当然也有李庚希。
似乎相对来说,作为绝对男一的范伟反而被夸赞得少了,这当中可能有两个原因:其一是范伟固然演得很好,但他一直以来就是这种高水平,正常发挥嘛;其二是王响这个角色过于复杂,难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同,也难逃「爹味过重」的指控,于是对角色的情感疏远,可能牵连了演员。
但我想说的是,对范伟的这种「沉默」,恰恰就是一种认同。
范伟在2005年辞别小品舞台,迄今已经十八年,期间他深耕影视谋求转型,很多层面都做得足够成功。对于他客观的演技水平,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曾经系统地分析过,因此剩下的问题可能就是:年过60的范伟还能不能再进一步,打破自身最后的演技壁障?
如前所述,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以文本来激发演员们的表演潜能,而不是反过来靠一个或几个演技派的全面发挥来盘活文本,后者必然是俗套和下乘,范伟在最近十几年商业片中就是这种状态;前者则是可遇不可求,一旦遇见了,哪怕是经验贫乏的菜鸟都能让人刮目相看,更别说资深演员了。
范伟的基本功是一种念唱打坐式的,这里最合适的例子就是《一秒钟》里的范电影,他推开影院的门、拿着一个搪瓷缸子出来,就瞬间成为舞台画面的中心,他有这样瞬间调整场景的外化能力,而且善用周边的器物(如香烟、花生米)来塑造自身。
《一秒钟》(2020)
他那一贯可识别的步伐、体态、节奏,都是展露给「戏台观众」的,会默认有一个身边不远处的观察者,这与同片中的张译大不一样——张译的舞台路数属于内心戏,讲求的是沉入角色,不需要那个观察者。
这样一比照,范伟的优势和弱点都很明显,他的大脸压得住很多角色,拿捏台词和节奏也极有效率;然而只要他还依赖这个戏台观察者(在我们看到范伟的时候,也潜移默化成了这样一个观察者),就无法更进一步。
这种问题不是范伟独有,也存在于吴刚这样的演员身上,以及人艺等机构培育出的一干老戏骨身上。他们中的一部分被视为演技高于范伟,也仅仅是因为在台词和腔调方面的功力更为深厚。
老戏骨们无法改变或者拒绝改变,但范伟是愿意改变的,这是《漫长的季节》传递出的重要信息。
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王响当然也有范伟过去角色的一些痕迹,比如说90年代的火车司机是工厂时代的「大师傅」,接近于《芳香之旅》中的老崔(包括他最后一集与张静初的重逢);2016年的出租车司机则是破落都市里游走的散人,比较接近于《耳朵大有福》和《看车人的七月》中溃败、无望、失魂的下岗职工。
《看车人的七月》(2004)
这两个身份,随着镜头的上下摇动进行着时空置换,从火车司机变成了出租车司机。这种运镜转场有着类似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残酷,当2016年的王响进入画面,他的消瘦和白发并非是单纯的岁月使然,而更像是命运的釜底抽薪。
范伟在演绎1990年代的王响时,带着一种确切的工厂时代的红润生命力,而一到2016年,他的形容就转为失神和木讷,即便在下一秒就可以转回他丰富的生命经验和应对问题的灵巧——但就是这一瞬间的魔怔、延迟,让范伟变得与众不同,他一贯的表演节奏发生了变化:不再需要那位戏台旁观者,观众也不再如往常一样能猜到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
第一集开头与龚彪验车的一场戏是两位演员双双打破舒适区的较量,或者说两人站在对方习惯领域内的较量,这不但是秦昊的胖与范伟的瘦逆转了视觉印象,也是因为人设、台词和节奏的错置——龚彪的台词充满了各种夸张性的、有意面对戏台观察者的展示,而范伟则舍弃了无效的对白和预设性的动作,进入了一种紧凑且随意的秦昊格外擅长的心理戏。
主创们没有按照范伟的特点来写角色对白,范伟也接受这样的改变。《漫长的季节》并没有着重于范伟的大脸特写,而是适度将其放在中全景,使他能够有机融入环境,而不是依靠他来改变环境。
有一种说法,每个国内独立电影导演心中都有一部《杀人回忆》,本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《杀人回忆》。
这不光是一种故事文本上的回响,镜头语言也是相当明确。或者说,这部剧的整体调度都有着韩国电影的诸多印记,对此东北的场景故事可谓是得天独厚,因为这是全中国最接近朝韩环境的地域,虽然本片事实上拍摄于昆明一带。
所以这不止是桦林,也是一种泛东北亚的生态,如果说整部剧在剧作力度和影像调度上更多向韩国电影靠拢,那么作为主角的范伟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参照物,那就是韩国影帝宋康昊。
《杀人回忆》(2003)
同为60后的老牌、大脸、丑萌男演员,范伟与宋康昊有部分共性,也有颇多差异,比如宋康昊能驾驭的一些类型片范伟就驾驭不了(两人差距更多是在形体方面),或者宋康昊更像是一个综合式的标尺,他的一部分在范伟身上,一部分在秦昊身上,一部分在陈明昊身上。
那种韩式标志性的轴,和潜在的大男子主义,三个人身上都有,范伟体现得最好。
因为陈明昊属于角色驱动,秦昊属于反着演,范伟身上则是具象实存。
这让他成为最大的悲剧承载者,就像王阳的死虽然是意外,但也是因为他的间接原因造成的,这一如《隐秘的角落》中老陈对严良「过于沉重的关怀」。
范伟在90年代情节中的段落,带有自己标志性的个性表演方法,并未去掉那个戏台观察者的特征,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也是《隐秘的角落》中王景春的延续,但在2016年的段落里,范伟实现了这种自我超越。
《隐秘的角落》(2020)
除了形容、节奏、台词上的变化,这个角色融入了超现实的梦幻特征,以王响和两个儿子的虚实交织呈递出一种类似阿兹海默症的征兆,说这是「困在时空里的父亲」也很恰当。
王响和王阳的关系,是无数中国父子关系的暗影,对一个爹味的父亲而言,丧子是最致命的报复,因为自此便没有了爹味的权力——这种「权力」,在本质上是由工矿企业、工人文化、硬件机器以及「大师傅」的自傲建立起来的。
当然这些只是剧中角色自身的特征,它自带内部批判,与主创逻辑无关,不必以此批评作品。如果「爹味」象征油腻,那么90年代的王响确实油腻,即便这种油腻不同于「大爷」那一类的油腻(在《第一炉香》里他也一样能演出这一类的油腻和猥琐),也确实割断了观众的认同。
2016年的王响抽丝剥茧一样追溯案件,是一场漫长的、不眠不休的赎罪,他形容枯槁头发花白,已经看不清脸部活动的肌肉群。观众对他的感觉极度复杂化,有同情、感叹、归咎,但更强烈的触碰在于他走在某种时空通道的岔口。
前两集的末尾都以王响的「睹物思人」嫁接其某种超现实景象,儿子还魂的一桌饭菜、垃圾桶下掏出的手术刀,是追思,也是梦魇重现。
即便有意作出这种改变,范伟仍然不会和过去的自己告别,在塑造90年代王响的过程中,他更多在集约之前的路线,以后和后一个自己拉开距离,也只有这样的「曾经」和「现在」并行交织,我们才能看出范伟改变了什么。
90年代是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场景和人设,人们甚至能看到他撑着伞在维多利亚门口和迎宾侏儒的对话,「维多利亚」是范德彪曾经当做保镖的夜总会,而面对迎宾员的「似曾相识」的询问,王响的回复是:「认错人了」。
2016年的现时是范伟演技精进的时代(剧集跨度的1997-2016则可以看做他的成名和奋斗史),他以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拿下金马影帝,开始向顶尖实力派迈进,在谋求「向前看」的过程中,他必然要同自己过往的一部分告别。
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(2016)
《漫长的季节》以范伟为轴心,借助各种情境和道具转场(尤其是红毛衣)嫁接起多时空叙事,范伟作为枢轴性的演员,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,他身兼很强的境遇和精神跨度,但却不大容易表面出彩,完全逆转了惯常的逻辑。或者换句话说,范伟将自己融入了故事情境,成为情境的墙纸背景,托出了秦昊和陈明昊两个耀眼的图形,而自己却被观者们相对忽略了。
《漫长的季节》就整剧而言,前半段优于后半段(可能这和很多评论者的观点相反),因为前半段主打的是人物情绪和记忆,后半部分则越来越倾向于情节流。
其中的一个原因,是范伟的重要性在后段走低,哪怕秦昊和陈明昊则以其强力填补了其中的角色认同也仍然不够,因为后两人的角色基本都是单向性的,唯有范伟扮演的王响才是拉锯式的。
比如在第11集,王响的悲剧(儿子去世和暴揍厂长)接连发生,意味着失去了父亲和工人的双重身份,而后面一个场景,是2016年他在出租车里和李巧云的三角恋浪漫告白。
前后两段中的范伟呈现为一种失魂、撕裂和康复的拉锯过程,这种过程在影片中对应家庭的破碎和重组,或许对那个「响亮的响」的工业时代爹味劳模来说,家庭血缘本身就是诅咒,倒是一种非血缘的家庭关系展示出替代性的疗愈功能。
范伟的自身拉锯式张力,也呈现为一种自我平行对照,这就是影片最后穿越玉米地的场景(这也是第一集最初场景的重现)。玉米地像一个虫洞,他看到了曾经的铁路,和曾经的自我。他追着远去的火车向过去的自己高喊:向前看,别回头。这是他作为角色的生命经验,也是他作为演员范伟不断进化的座右铭。
在花甲之年遇到《漫长的季节》,对范伟来说是一种幸运,但也是一种回馈,一如剧尾的瑞雪。自从他坚定地从舞台转投影视以来,就有一种不止不休的动力。
抛开那些为求生计但仍然堪称演技范本的角色之外,范伟的演技更多是伴随着那些影视精品不断进化的,比如《芳香之旅》《耳朵大有福》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等等,如果这种动力和机遇能够得到延续,那么范伟对自身演技甚至自身物理条件的开发,仍然存在新的可能性。
60岁阶段还保持着进化状态,这样的演员,华语影视圈应该没有第二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