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的雨下得很频繁,村子里难免会传出难以置信的说法。
雨中撞见行走最可笑的无头鬼,就是算命老头在村口坐着打锣骗钱这种行为,看着真是可怜!可怜是看在手如同一截老槐树枝一样硬,行道上很少有人他却喊“请勿雨中漫步,有声速速归也……”
忽远忽近地哭泣声,给梅雨间的田野带来一份神秘的面纱。农伯如临大敌刚经过耳畔就传了哭腔的声音,看着清晰残留可见的鞋印,很显然是刚留下得,这很难不让人好奇。他慌乱搀扶着裤角,头戴的斗笠也跟随身子晃动,闻声过后他踏进断崖式的泥土道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农伯站在水沟旁的稀泥上,漏出非常平静的一张脸,沾了泥的眼角透露出愉悦的神情。摸胡子的同时,滑溜溜得雨滴也顺斗笠落在袖套上。
胆子是用来衡量人的能力,仅此而已。
“嘿呀!声音像是小孩子,这大雨天难不成?”,他迈出的步伐实在是稳健,“老夫在下乡活了大半辈子,还没打滑过!”
头也不回地农伯沉淀淀的去寻找声迷之旅,不忘还撇了眼田野。
承受着风雨交加的水稻成排的仰着身,上帝揉捏它们地脊背,背影后方则是阁楼屹立在杂草中,大水蚁畏缩的趴着,宁静的看着一片放眼望去的田野。
雨不断循环,他轻巧得往有声的地方靠前。还时不时挑起三角斗笠,要靠近水稻边的农伯伸出带有泥屑的手摸了摸腰间的镰刀!
“谁!”农伯矮瘦的身子,望向水稻下。视线被水稻遮住他疑惑的自我回答,农伯咽了口唾沫,如同一颗小石子咽入喉咙下。随后缓缓地走过去并收紧镰刀,裤脚因此也打湿还带有泥,雨下的大了。
女孩蹲在地上长发披肩顺着下去,一身穿着酷似嬷嬷的打扮。暗淡的服饰和脸上摆出耐不住的样子,看起来是穷苦家的孩子在找什么东西;他将手背在背后,漏出的气愤瞬间收了回去。女孩开口了:“啊……”带着“普勒效应”的声音,“跑掉了?好可惜。”
“下这么大的雨你在这做甚?”他感觉太奇怪并没有在意女孩挖泥巴,手也是紧紧捏着它,“你刚刚哭了?雨声中我也会听见。”
她观察着刚挖出来的坑,“我父亲说这下雨天黄鳝都活跃在附近,让其多抓几只。”
女孩翘起眼睛看着他,眼眶很红。秀发湿透的过后少余得粘在肌肤上。
“下这么雨,不怕感冒啊!”他知道是为什么,但嘴里忍不住就说了,“来,先把斗笠戴上会好很多。”
她嘴角微微撅起,神情散发出神秘和梦幻般的空白聚集在女孩周围,“怕,不听话会被修理的……”此时的女孩委屈得低下头。
“谁会……”没等农伯说完就回答到‘我爸爸’ ,看来是个行为恶劣的父亲。“他姓什么?”
女孩看向农伯的后方,犹豫了几秒:“我不敢说。”
“这样啊!”她的裤脚露出条状红肿印迹,就没再过问,“那就不过多打扰了,不过你这样别提抓黄鳝了连蝌蚪都捞不着。”他展示出刚刚藏在背后的镰刀,“要想有收获就得找有效的方法,不仅快还顺畅”这朽烂的镰首,看着用了有不知多少个年头。
女孩开始思考这位悠然时摸胡子的大叔,刚刚就是这样。不过看着他也被琳的很厉害,说道:“俗话说水则清,自然无鱼。慢慢地总有收获。”
他有些不知所措,这时起了微风沙沙吹过凌乱的叶片,雨滴也敲打在斗笠上。
两人一起却形成了两种极端,农伯不自觉的发抖而她却安然无恙的挖着泥巴,泥巴做成了大小不一的小人。
想安抚女孩的思绪被脊背莫名的发凉所畏惧,久说无果想要道别时,肢体不知接触到跟缝针一样。就这样不快不慢的扎进去,那时的水稻仍然树立在他面前,但又不见底部只见一片乌黑的天空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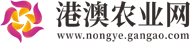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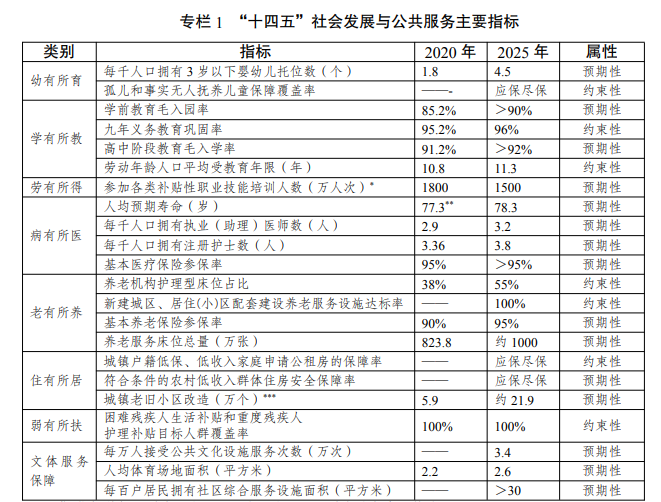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![魔兽世界电力网任务在哪_魔兽世界[电力网]任务怎么做-全球热推荐](http://img.xhyb.net.cn/2022/0923/20220923104618738.jpg)



